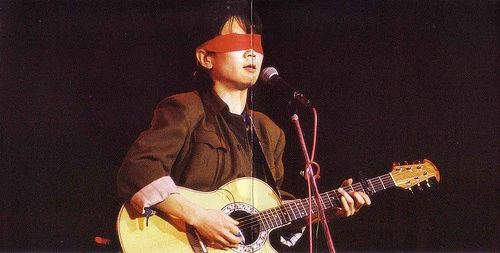2013 年发光曲线乐队在南京新古堡酒吧的演出让我终身难忘。
两支嘉宾乐队中的其中一支名叫 「塑料司令」,是由两人组成的后朋乐队。由于后朋风格的受众原本就不多,加上现场观众人数屈指可数,便出现了观众围观他俩演出却毫无反应的尴尬场面。
在演出结束后,其中一名乐手情绪失控,冲上前对着话筒喊道:「南京没有摇滚,在座的都是傻逼!」 另一位乐手见状,上前冷冷地补充道:「你们要是站到这台上,就懂这是什么意思了。」
由于最开始并没有介绍环节,我和朋友直到演出结束都不知道这些气急败坏的跳梁小丑究竟是谁。光阴飞逝,当年的场景早已变得模糊,但是这句话倒是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早在 《乐队的夏天》 开播前几年,就已经有不少个人和企业组织乘着新媒体的东风踏足摇滚乐。这些新媒体们常常把魔岩三杰唐朝黑豹等一众摇滚老炮的事迹翻来覆去地发表,为的就是吸引部分传统国产摇滚乐爱好者。自然而然地,在这些文章下总是会有一些怀旧的读者发评论感慨 「中国摇滚已死」,「再也回不到当年的辉煌时刻了」。每每看到这类言论时,我都会想起多年前新古堡酒吧里的这一声怒吼。
摇滚是什么?它死了吗?
在大学时我曾操办过一次乐队毕业专场演出,为了录制宣传视频而向队友发出灵魂拷问:「摇滚是什么?」 队员的回答五花八门,有人说摇滚是一种 「不向主流妥协的精神」,也有人说摇滚是一种 「坚持梦想的态度」。现在再回想起来,这些回答幼稚中带着可爱,因为大家只是在变着花样解释自己为什么坚持玩乐队而已。为自己喜欢的事物赋予精神含义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这样便能将自己的喜好与他人进行量化和区分,以便找到志同道合之人。年少的我们都是这样一路走来,这无可厚非。
但摇滚不应该如此复杂。这几年随着自己看待事情的角度不断拓宽,摇滚在我眼中最终简化成了一个纯粹的音乐风格概念。音乐风格当然是不会死的,它会永远活着,并伴随着下一个音乐潮流的来临而激发出新的活力。
有意思的是,摇滚、民谣、说唱,喜欢这些风格的人们都在强调它们 「真实」「批判」「不妥协」。然而当各类音乐风格,甚至其他诸如文学和绘画之类的艺术形式都相继被贴上这些标签时,那么一再强调 「批判精神」 又有何意义呢?
但是我不会否认 「摇滚精神」 的存在,它确实存在于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社会氛围中。当一个音乐风格概念上升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我们必然要联系其所处在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进行讨论。
上个世纪随着二战结束,世界格局发生剧烈变化,美苏冷战令局部摩擦不断。在这种环境下摇滚迅猛发展,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也带上了当时流行的反战与反主流主题。中国的摇滚乐始于八十年代,当时中国对外开放,国人生活在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陆摇滚乐也因此烙印上了对剧变的迷茫与反思。现在回望当时所谓的摇滚精神,其 「批判」「反主流」 的主题实际上是那个年代社会环境和人们思想观念变迁的真实写照。
而在当下,随着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数量众多的摇滚作品里所要表达的主题也开始变得多元化,囊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难以概括提炼成简单的概念。如果一定要归纳当代的中国摇滚精神,我愿意理解为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与此同时,摇滚乐产业逐渐发展起来,走近人们的生活。迷笛学院在培养大批音乐人才的同时举办了一届又一届的迷笛音乐节,慢慢地带动了音乐节产业在全国各地开花。据大麦网 《2020 演出国庆档观察》,仅 10 月 1 日到 8 日,全国各地大小音乐节就有 20 余场,票房比 19 年同期上涨了 113%。音乐创作方面,越来越多的独立音乐人开始制作摇滚乐,在音乐平台上上传自己的作品,拓宽了宣传渠道。网易云音乐发布的 《中国音乐人生存现状报告 (2020)》 指出,网易云音乐人已超 20 万,其中有超 20% 涉猎摇滚乐创作。另一方面,摇滚乐也成为综艺娱乐新的试水点,从 09 年的 《百事群音》,到 12 年 《虎牌乐队龙虎榜》,再到近几年 《乐队的夏天》、《中国乐队》 等,进一步推动了大众对摇滚乐的认知,使得摇滚在中国不再小众。
在这种环境下,我很理解部分人面对海量音乐人和作品时出现 「淘歌难」 的困境。他们无法像过去一样轻松地找到符合自己口味的摇滚乐,因此凭着自己的主观感受,很容易将问题归咎到产业上,认为中国摇滚没落了。但是跳脱出狭隘的主观感受,我们能看到的是中国摇滚乐市场的飞速增长与日渐完善,音乐创作主题与风格的越发多元化,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可以搜索到各种风格的歌曲,可以在千里之外随时关注感兴趣的乐队动态,可以更加便捷地购买演出门票。对于音乐人和乐队来说,在音乐平台可以便捷地发布作品并获得收益,也可以在后台看到各式统计数据,更加全面地了解自己的受众。
回到开头,如果塑料司令乐队还活跃在这个时代,他们完全可以根据音乐平台提供的粉丝数据,依据其年龄、地域分布来规划演出路径,并进行更为精准的定向宣传,一方面规避掉人少的赔本演出,另一方面也能吸引到更多喜欢后朋的乐迷与他们进行现场互动。你们说,这个时候,他们还会再说出 「在座的都是傻逼」 这种气话吗?
愿摇滚遍地开花,在座的都是牛逼。